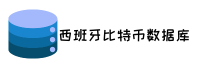我知道几十年逐步推行,几乎没有支持者,但我坚持己见。公众应该首先戒掉那些没人在意的拼写。不要再区分 – ise和 – ize ,用 – or代替 – our,就像美国已经做的那样。去掉真正没用的双字母,尤其是词尾(till、spell等等)。如果pus 的分泌可以不受书写意象的影响,那么 less的拼写(如果是les )的影响或许也不会减弱,而且(真是糟糕!)大多数人可能会同意, mean的过去式(如果是ment)不会被当作mental的词根或同音后缀。这里不适合推行整个方案(我),但我的想法显而易见。即使是最坚定的保守派也可能会耸耸肩,同意如果till和until看起来是相关的词(它们确实是),我们的社会可能不会崩溃;如果我们能忍受stir和whir,我们就能忍受er和pur(err和purr)。我迫切地想看到第一步:英语世界就立即采取行动的必要性达成共识。革命性的计划,无论多么巧妙,都只能是计划,而不能称之为行动。或许,计划中的国际拼写大会能有所作为。我依然抱着一线希望。
民主党共和党
一位记者一直在研究这个专栏标题中给出的术语的起源。他写道:“据我所知,这个术语在20世纪初开 最近的手机号码数据 始使用,或者可能更早一点……它似乎是大约一个世纪前由民主党附属学者创造的,他们希望宣称从杰斐逊到杰克逊,一直到现在都有直系血统。” 这封信要长得多,但从我复制的段落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它的主旨。现在我将引用它的结尾:“那么,是谁干的这件事?这是我的问题。如果你能回答我会很惊讶。如果你能,我会很高兴。” 唉,我所能做的就是把这个罐子踢到路上,就像现在的政客说的那样。有人能处理这个罐子吗?
虫子和巴克
在我关于bug的帖子中,我提到了bg名词组成的一组词,其亲缘关系有时很难确定。问题是bk组是否具有类似的特征。我认为有。因此,重复我的老例子,英语bug “bogeyman”类似于俄语buka。所有此类新词听起来都像婴儿词。问题是,只要我们不超出一种语言的界限,引用婴儿词是可以的,但它们是如何传播到广大地区的?它们是在任何地方独立创造的产物,还是某种神秘传播的产物?单源论还是多源论?那些可以查阅我的词源词典的人会在词条boy中找到对这个问题的完整讨论,这个词的“词源争议”很大。
如果英雄们失去了头发,会发生什么?难以想象
如果英雄们失去了头发,会发生什么?难以想象。
麻烦的代词
摘自报纸:“6月18日,一位写信人问,如果一个学生掉了头 印度手机号码 发会怎么样。”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,但在重读乔治·艾略特的《米德尔马契》(我年轻时不喜欢这本书,现在更不喜欢)时,我注意到她区分了自己和人物的用法。这部小说写于19世纪70年代初。西莉亚谈到她姐夫时说:“我觉得他对多萝西娅的喜爱还不够;但他应该够爱的,因为我肯定没人会喜欢他——你觉得他们会喜欢吗?”另一个角色(所罗门·费瑟斯通)问道:“有人可以问问 从人道主义者到官员 他们的兄弟说了什么吗?”这又是西莉亚说的:“我们怎么能活着,却以为别人有困难——那种撕心裂肺的困难——我们能帮助他们,却从不去尝试呢?”(1986年克拉伦登出版社版第278、304我提出的拼写和783页)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,她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总是这么说。
英语习语